仓颉之“颉”应读“jié”
文章字数:1,6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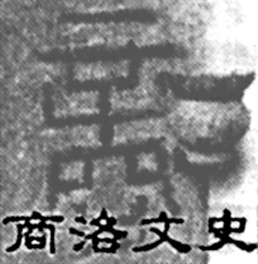
★郭敏厚 下 篇三、仓颉之“颉”曾叶(xié)音为“系”(xì),不足为据 《康熙字典》对仓颉之“颉”音还有一解:颉又叶胡计切,音系。卫恒《四体书势》:“黄帝之史,沮诵仓颉。眺彼鸟迹,始做书契。” 《康熙字典》的编者以为所引之《四体书势》乃四言诗,二、四句末之“颉”、“契”当为韵脚。但是“颉”在《广韵》中分别读“胡结切(jié)”或“奚结切(xié)”,“契”却读“苦计切(qì)”。(因为,反切上字“苦”的中古声母为“溪”,音k。元代进入北京音系后分化为k与q,此处应读q。反切下字“计”的韵、调,读音相当于ì。)两者不能叶韵,于是便采用宋代朱熹那种强改字音、以就今读、使之叶韵的方法,人为的改“颉”之本音为“xì”,且用直音法标音为“系”。 《康熙字典》强改字音的叶音法是唯心主义的,然而《四体书势》的确是段韵文。卫恒(?—291)是晋代书法家,所处的时代应属汉语史的上古音时期。音韵学家依据《广韵》中之中古音,向上可以推出上古音。所以,查阅《上古字音手册》(唐作藩著)等工具书,即可知:“颉”的上古声母为“匣母”(国际音标为[γ],相当于振动声带的h);韵部为“质”(国际音标为[et],e相当于普通话“梅”méi中之e,t为入声韵尾,只表示音调短促);“契”的上古声母为“溪”母(国际音标为[k],相当于k),韵部为“月”(国际音标为[at],a相当于普通话 “担”dàn中之a,t亦为入声韵尾)。“颉”、“契”两字韵部不同,看似不能押韵,但“质”、“月”属相邻之入声韵部,[et][at]发音接近,可以转押近韵。这种宽押,音韵学术语谓之“旁转”。“质月合韵”,在王力先生的《诗经韵读》一书中多有出现。 语音是变化的。“颉”、“契”之上古音到了中古《广韵》之中,早已面目全非,无法押韵。所以,《康熙字典》便采用了形而上学的叶音法,注“颉”为“叶胡计切,音系”。此音既非上古音,又非中古音,故而作为“颉”的读音,不足为据。其它字书均不收。 四、按“颉”的声符,读“颉”为“吉”,乃是误读 《说文解字》(东汉许慎撰)对“颉”之注为: “颉,直项也。从页吉声。” 下无注音。宋初徐铉校订此书时,依据《唐韵》加“胡结切”。 “从页吉声”,表明“颉”是形声字。“从页”是指形符是“页”。形符表示该字的词义范围。“页”是人头,那“颉”的词义就在“人头”这一范畴之内,是直脖子。人名多取此义,表刚直不阿。声符表示该字造字时代的譬况读音,不一定与该字读音相同。即使当时相同,由于后世语音发展变化,也早已不同。所以遇上形声字,切不可以丰边声符定读音。 查阅《广韵》,即可发现早在中古之时,颉、吉已不同音:从前文已知,在《广韵》中“颉”为“胡结切”、“奚结切”,读jié、xié;而“吉”为“居质切,入质见”。即反切上字“居”的声母为“见”,中古音为g,今为j;反切下字“质”的韵调为入声质部。元代以后,入声消失,变为去声,所以“质”的读音与今天ì差不多。上下二字相切为 “jì”与“颉”音完全不同。 此外,《广韵》在“吉”所在的“居质切”中, 还收有以“吉”为声符的其它一组同音字, 如“趌、狤、拮、郆、”等,却未收“颉”。这也告 诉我们,中古之时“颉”以不读“吉”。 既然如此,又有人提出质疑:那是不 是可以认为“颉”今天就可以读前文所说 的上古音“匣好[γ]、质部[et]”了呢?我们以为语音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的。尽管人名一类专有名词的读音有很强的稳固性,但一个人名是否要按古音读,其决定因素是要看其是否有古音流传后世,而不能按今天音韵学家依照语音发展规律向上推断出来的上古音专读。比如,《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有 “郦生食其者……”,唐代学者张守节即在文后注:“历异几三音也。”即是用直音法指出“郦食其”应读为古音Lìyìjǐ。然而,《吕氏春秋·君守》、《荀子·解蔽》、《韩非子·五蠹》等书中都出现过 “仓颉”之名,但为三书分别作注的汉·高诱、清·王先谦、王先慎等均无只字为“颉”注特殊读音。可见,“颉”无古音流传至今。所以,今天只有“jié”音才是仓颉之“颉”的正读。(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