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 山 行 吟 者
文章字数:2,4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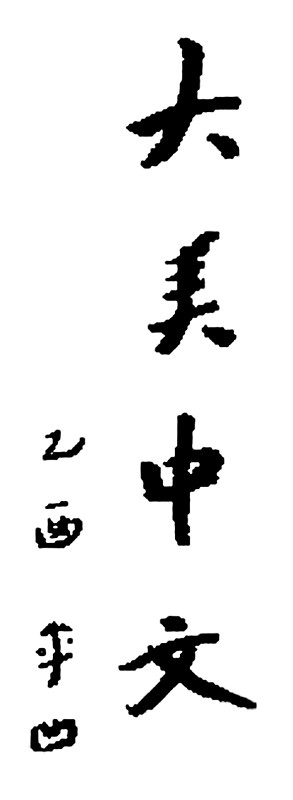
★黄元英 (接上期)(三)惨烈的改革者商鞅 商鞅变法及其“秦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之事,家喻户晓,商鞅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肇始于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当然,商鞅改革的创举令人敬佩。但以愚之见,商鞅是个惨烈的改革者。 元丰三年(1080)九月十五日,苏轼阅读《战国策》之后,写了一篇《商君功罪》的读后感,指出商鞅搞改革之失:“然其民见刑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后之君子,乐言商鞅之功,“而忘其祸之惨烈”,“吾为之惧矣”!他甚至将褒扬商鞅列为“司马迁两大罪”之一,并说“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苏轼集》卷92、105)。 2011年6月1日《新民晚报》刊登毛泽东18岁时写于湖南省立一中(今长沙市一中)文章 《商鞅徙木立信论》,对徙木立信提出质疑:“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国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因为,徙木立信不是为了建立社会诚信让民众互信,而是让民众相信商鞅说话是算数的。这行为显然有炒作嫌疑,暴露出作为变法操盘手的商鞅对民众的信任缺失和愚民思维。心中没有民众,改革何以成功? 苏轼的批判和毛泽东的质疑,看似没有联系,其实都指向商鞅变法失败的本质:对民智的漠视,对人性的撕裂,对功利的膜拜。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需要吃穿更需要讲人伦。商鞅改革彰显了前者,却毁杀了后者,“民见威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使人成为残缺之人。在他看来,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都是国家“六虱”之害,是影响各级官员执政能力的祸根(《商君书·靳令》)。商鞅以斩断文化之根、撕裂人性亲情之举,成就秦王所谓帝国之梦,何其惨烈!当商鞅落作法自毙,才慨叹“为法之敝一至此”!但,迟到的醒悟已无法挽救“车裂”和“灭商君之家”的惨烈结局!那一声哀叹,如激越而狂躁的乐曲残章,凝固在历史的上空,记录着痛楚扭曲的表情和夕阳倒映在泪和血中的画面,又似乎在表达着某种祝愿和期望。(四)梦断商於的熊槐为君执政30年的前楚怀王熊槐,怎么也想不到,人生命运的转折竟然与秦头楚尾的商於之地有直接关系。 怀王执政时,秦、楚、齐大国三角关系业已形成。“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战国策序》)亦是人尽皆知。前313年,秦欲伐齐,张仪南下说楚,以“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为诱饵,要楚断绝与齐国联盟。“怀王大悦,乃置相玺於张仪,日与置酒。”张仪返秦“称病三月不出”。怀王在等待中又派勇士“北辱齐王”以示对秦的诚意。结果促成“秦齐交合”,此时张仪让楚将军受地“从某至某,广袤六里。”这著名的“张仪诈楚”事件,见于《史记·楚世家》、《战国策·楚策》等史籍中。张仪这一诈,诈毁了楚怀王的智商和情商,炸毁了楚族的尊严和声誉,也使楚国失去理智而连吃败仗。商於之地成为怀王挥之不去的梦魇和奇耻大辱! 14年后,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在商於古道上。前299年,楚怀王收到秦昭王充满温情的信:“始寡人与王约为弟兄……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质於齐以求平。寡人与楚接境壤界,故为婚姻,所从相亲久矣。而今秦楚不欢,则无以令诸侯。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屈原等人劝怀王不要赴约,未被采纳。虽知,秦昭王没有如约到武关,却“诈令一将军伏兵武关,号为秦王。怀王至,则闭武关。”怀王被押至咸阳,悔之晚矣,“卒于秦”。这一次,秦将关闭武关之门,也关闭了怀王的政治之门和生命之门。武关,竟成为前楚怀王有去无回的生死关。 怀王“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皆“人之祸也”(《屈原贾生列传》)。是啊,假如,怀王拥有基本的智慧,不被欺,不赴约;假如,昭王、张仪讲诚信,郑袖、靳尚不背叛;假如,屈原能继续“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怀王、屈原、楚国的命运、战国争霸的结局,乃至中国史学、文学的叙事,都会有另一种可能。但是,见证了上述悲剧的商於之地,千载不变地重复着一个忠告:历史和人生不承认“假如”!(五)秦始皇首次东巡在武关落幕欣赏河山?宣扬君威?压治东南天子气?反正,嬴政灭六国后很喜欢出巡。出巡前,做了很多准备,先是更换名号,因为“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嬴政自以为功绩超过三皇五帝,与大臣议定尊号为皇帝,天子自称朕,民众称黔首;再就是“筑甬道”,“治驰道”。 公元前219年,在王贲、隗林、王绾、李斯等文臣武将陪同下,秦始皇开始了他的首次东巡。《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随行人员商议决定将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琅琊石刻在歌颂 “皇帝之功”、“皇帝之明”、“皇帝之德”的同时,还有宣传“器械一量,同书文字”重大决策,开展“匡饬异俗”、“除疑定法”思想教育以及树立“忧恤黔首”、“泽及牛马”良好形象的巨大作用。如此,东巡就成为高明的执政行为。但是,这一路上,始皇只是为求仙人、寻周鼎和伐湘树三件事用了心思、出了大力且动了龙威。这才明白,那石刻原来是出色的文宣,对那些随性人员的笔杆子功夫不无羡慕。 在琅琊,始皇“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到泗水,“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据传夏禹继天子位后,用九州所贡之金,将各州的山川形势、奇神怪兽铸于九鼎,九鼎就成了国家重器和政权象征。《左转》就载有“问鼎中原”的典故。始皇听说有一鼎沉没在泗水,虔诚斋戒后“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遗憾中继续南下,渡湘江时狂风大作,波涛汹涌,差点过不了湘江。岸边有湘山祠,始皇以为是祠中供奉的湘君作怪,“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给山剃光头,以发泄江中遇险之怒,这位始皇帝一不小心又开创了天下第一。接着,《史记》索然无味地写道:“上自南郡由武关归。” 始皇高调东巡,在武关悄然落幕。史书没有记载秦始皇过武关的细节。武关却因迎送了大人物、见识了大场面,而名声远扬。(作者系中文系教授、商洛民俗文化研究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