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版内容
文章字数:3,7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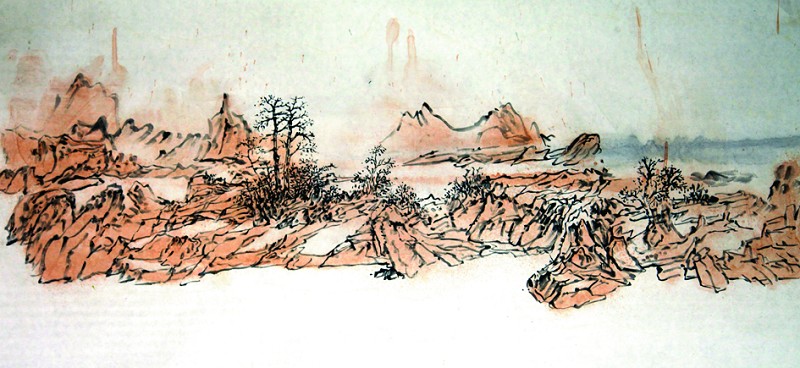

老银匠 ★陈敏 老家镇子有一个小银匠,姓易,银饰手艺做得精湛。除了做银饰,他还打铸一些其他金属物件,如小孩子的铜碗铜勺铜手镯,女人头上戴的铜发簪。也有极少数富贵人家拿来黄金请他打金首饰,不过那样的顾客很少,一年也碰不上几个。 小银匠的匠铺一早就有人来访,访客基本是女人,媳妇姑娘居多。他们从布包里掏出积攒的财宝,请他做首饰,当然还有什么也不做的女人,她们在家待闲了,也来凑凑热闹,看小银匠干活。时间一长,小银匠便成了以女人为对象的手艺人。 女人们大多热衷于和他交流。她们戴在头发上的发簪,手上的戒指都因有了小银匠的一句赞美之词而变得美丽而踏实。 也有投来怪异目光的,在弥漫着流言蜚语的小镇,忙碌在女人堆里的小银匠不久便迎来了他生命中的一次惨痛。 一场动乱风暴呼啦一下扫来。小银匠的店铺被一帮“红袖章”砸得七零八落。他被带上了一顶纸高帽,成了审判台上的罪人。 造反头子给他拉了个黑名单。黑名单里列有48个据说是和他有染的女人。万人批斗大会上,48名女人按名册一一揪出,被一起推上审判台。台上台下,人声如潮。突然,声浪戛然静止,当众多的目光一一扫过台上的女人时,很快发现48个女人中竟然有4个是男人。 4个男人因叫了女人的名字而被列了进去。小银匠也因证据不确凿被推下了审判台。 造反派们自然不甘心自己的疏忽大意,他们拿起小银匠曾用过的、起落了无数次的锤子狠狠敲击他的小腿。一阵千锤百炼过后,小银匠的一条腿瘸了。 小银匠向老银匠的过度似乎只是一夜之间的功夫。他突然变成了一个小老头。 在无奈黯淡的日子里过了数年之后,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重操旧业,接为数不多的活计。接到银料后,反复捶打,再经过7到9次回火,以消除捶打后的杂质和印痕。这门手艺在他手上断断续续维系了将近30个年头。 世间一切手艺都有一个相似的命运:它们会在不知不觉间湮灭于历史的长河中。很多镌刻着历史印痕的传统手工艺在其演进中慢慢退出了舞台,匠人们也不例外,他们也会随之而隐匿于尘埃之中。而固执的老银匠顽强地坚守着他的银匠阵地。他说他不健全的腿,让他走不远,所以,他就不走了。他要留下来。 不善言谈的老银匠,天亮起床。他专注做活,默然化银,仔细地锉除粗糙,反复地锤击敲打,用手中无数次起落的锤子延续着这门手艺的最后存在…… 做一个手艺人,手里有活干,心里就踏实,心里一踏实,脸上就显得安宁与慈祥。那些砧子、钳子、锤子、锉子,还有各式的模具,冰冷着手,却温暖着心。 艺人自古命途多舛。 老银匠命运突然在某一天又发生了转折。转折是巨大的,他压根就没想到。 他的头上突然戴了一顶非遗承传人的桂冠!他被评为国家级工艺大师而成了被重点保护对象。 有富商出巨资,专门为他买下了一条街,要将他的手艺传承下去并将他放在街道最繁华处做演示。 许多眼睛和面孔一齐朝向他打银器的手,他青筋暴起的双手在众目之下像风中的树叶,抖动不止。 老银匠彻底老了。皱纹堆砌的面孔,深深塌陷的眼窝,瘦削单薄的身子似乎都在传递着他生命的最后气息。 有人问他每天还能出几件活儿,他说一件也出不来。人们疑惑追问原因。他说,我以前在我的铺子里自由自在,想出几件就出几件,现在,人像耍猴一样把我放在大街上,我哪儿还能干出活呢? 老银匠不久就去世了。 老银匠只做了三个月的大师就离开了人世。他的手艺却没有传承下去。但人们却记住了他,一个坚守到最后的好银匠。(作者系商洛小小说家、中文系教师) 七律·迎春花 (一) 条条青曼挂霜时, 朵朵黄花弄俏枝。 为报人间春色早, 风骚独领众芳姿。 (二) 一路先锋生来娇, 凌风斗寒舞雪飘。 敢为二月披金甲, 与杏和桃唤春潮。 (作者系艺术系2012级学生) 当爱已成往事 ★王 琳 《十八春》是张爱玲的第一部完整的小说,我们知道它的名字也叫《半生缘》,它有一种旖旎的美,但《十八春》无疑更加合适这个故事——十八个春天已将过去,一生中最好的念头已经不再了,这种怅惘,这种漫长,其中的酸甜苦辣又岂是一个缘字说得清楚的。在此之前,她也写过一部《连环套》,未写完就夭折了。奈何如今网络发展过快,只需要鼠标轻点就可以看见一篇好文章的关键词句。关于这部作品,最多的词竟是遗憾。 曾经编写了 《中国现代小说的光与色》一书的学者金宏达老师的《再看十八春》中说道:这部书对于张爱玲的创作生涯有一种特殊的意味,今天《十八春》吸引我们的,也不过是旧社会几个年轻人的恋爱遭际而已。于是我一直思考,这本书究竟哪里吸引着我们? 很多人说,男生少看张爱玲作品,看多了会添不少阴柔。可是我所感受的却是她笔下人物的生命。无论旖旎还是坎坷,无论巧遇还是错身,终究是细致的笔触和美。 它描述的不过是最平常的生活。就如同我们立身的是狭小的天地,经历的不过是最平凡的人生——顾曼桢不是绝世佳人,没有一顾倾人城的惊艳;沈世钧也不过是世上平凡的男人中的一个。这样两个人,连爱情都是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他通过朋友认识她,有点一见钟情的他尽力为她庇护。她在下班后和他吃饭,聊天。爱情是蝉,一早就出生,沉寂很久之后就能叫一个夏天,所以爱情一旦发生,真的没有办法抵抗。他们在咖啡馆外站着,顾曼桢或许紧张地搓着手上戴着的緑绒手套,世均默默地对自己说,一会一定要吻她。她写长信给他“我要你知道,这世上有一个是永远等你的,不管是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反正你得知道,总有那么个人。”连子通先生都说这是张爱玲笔下少有的温情。 一切顺理成章都不会来的如此轻易。这就是张爱玲惯用的笔法,后来写到顾曼桢被幽闭,两人错过各自拥有各自的生活自是得心应手。张爱玲为我们描述了一场红尘之中的悲剧,任何情真意切的缠绵都抵不上物是人非的残酷。沈世钧和顾曼桢的爱不是不深切,而是一不小心就被钻了空子。 她作品中的人有喜有悲,让人爱又让人恨。曼路因为一时之利陷害顾曼桢,却让人恨不起来。她也不过是个柔软的姑娘,只是想得到的东西太多。她和心爱的人见面时也是心如刀绞,只叹世间无奈太多,时光蹉跎。 爱情太脆弱。顾曼桢和沈世钧分别与不同的人结婚,爱依稀还在,只是故事也该结束了。因为即使回到从前又能怎样呢?时光催人老,时隔十八年,当年的情话现在看起来多可笑。 正像陈奕迅唱的那样,闭上双眼你最想念谁,睁开双眼身边竟是谁。他和曼桢相识,已经是多年前的事情了,算起来竟也十八年了。那初见时候密密匝匝盛开的花朵,也该落了。(作者系外语系2010级学生) 窑洞里的陕北 ★张辉祥 平凡,或许可以认为是一种“苦难哲学”。每次翻阅《平凡的世界》,读上几页便觉心沉,我知道,路遥是在阐释苦难,用陕北人特有的质朴,带着浓烈的黄土情怀,执着地倾诉生活的本色。只是,那些事情,那个年代无法走进我的记忆,但对陕北,早已“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永远是心神向往。 长假,出游,一路风景到陕北,大红枣、宝塔山、壶口瀑布、黄土高坡、窑洞,一切都是那么的淳朴自然。其实,延安之行,感受陕北就是品味窑洞里的陕北,让钢筋混凝土中滋生的城市浮躁在一方黄土中掩埋,用陕北的苦与朴,铸就一份旷世的超脱。 拐过一道黄色山梁,壶口瀑布的咆哮渐渐远去。可是,我依旧心潮澎湃,那半山坡上的窑洞里传出了气冲云霄的古老歌谣。是信天游,一声入耳,荡气回肠,连同陕北人头上那白羊肚毛巾一起包裹着无尽的苍凉与悲壮;是秦腔,吼出了城阙辅三秦的气势,那高亢的声音穿透了窑洞上方的黄土,使“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忽然明白,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人们之所以生生不息,就是因为窑洞里生长着一种不屈的力量。 陕北的窑洞,简朴中孕育着乐观,闪耀着“延安精神”的光芒,矗立着历史的丰碑。在王家坪,在杨家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窑洞处所,空间狭小、光线昏暗、陈设简单,可它却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土窑洞里的小油灯,点亮了一篇篇决定国家命运的光辉著作;窑洞壁旁绑着铁丝的床,顶起为了信仰而永不趴下的身躯;窑洞窗户上悬挂着的串串红辣椒、黄玉米,那是南泥湾屯垦的收获。我想,革命年代的陕北,运筹帷幄的“帷幄”不是军队的帐幕,而是一排排土窑洞,那里汇聚着革命的热血,涌动着革命的思想,丰富着革命的生活。 陕北人平生有两件大事,一是要有儿子,二是要有自己的窑洞。或许,一个窑洞就是一生的心血与积攒。所以,修建窑洞马虎不得,大有讲究:看风水,择地形,要向阳,背靠山,面朝开阔地带。陕北的窑洞,户型好,设计合理。从外面看一排窑洞,几孔窑,各开各的门,好像互不相干;可进入窑洞内,却发现有隧道将整个窑洞连通,成为一个整体,融合着家庭的亲情。 窑洞虽小,可别有洞天,透过窗户,外面便是那壮丽的陕北黄土高坡。因而,窗户就成了整个窑洞中最讲究、最吸引眼球的部分。窑洞是拱形的,窗户也就只能是拱形的,且洞口挖多大,窗户就开多大。一色黄土,容易视觉疲劳,为了丰富色调、美化生活,手巧的陕北人爱用窗花装饰点缀窑洞,于是剪纸成为一门艺术。逢年过节时,男女老少都拿起剪刀,买来五彩的纸,根据窗户的布局,光线的强弱,剪出“年年有余”、“龙凤呈祥”、“万事如意”等各式各样象征吉祥、富贵、平安的窗花。窗花一贴,陋室生辉,光、色、影的和谐之美得到了充分的呈现。 窑洞里的陕北,是平凡的世界,但它秉承淳朴、敦厚、隐忍的性格,可以面对一切苦难的折磨,可以承载一切生活的重负。陕北之行,我读懂了苦难,读懂了路遥,读懂了他为什么当年要扎根黄土,因为在窑洞中可以洞若观火,明白人生的意义。(作者系本报四川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