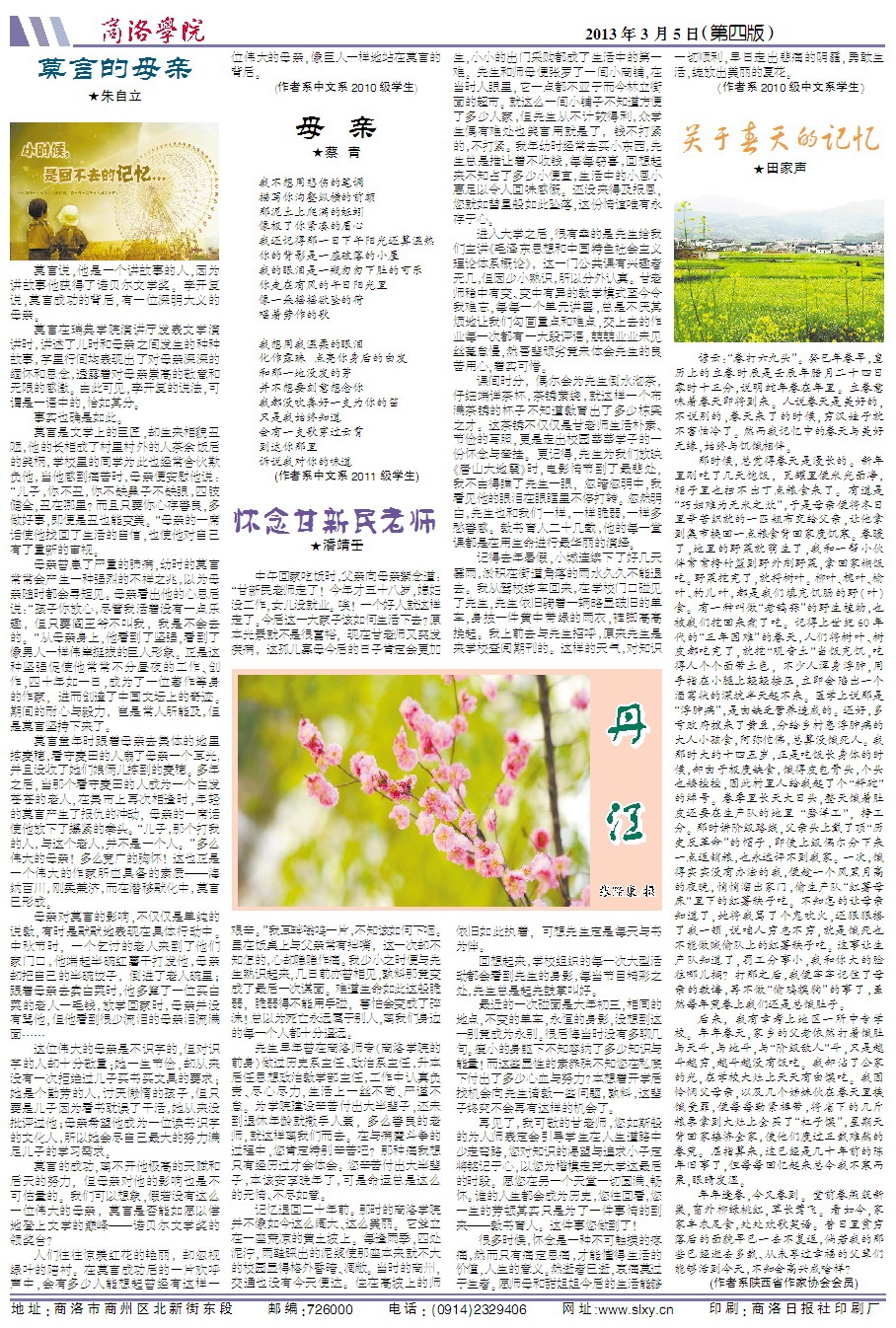第四版内容
文章字数:4,2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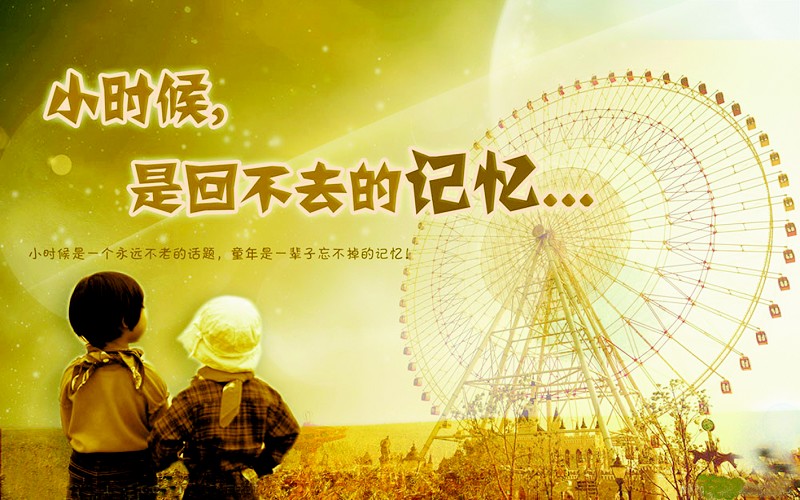

莫言的母亲 ★朱自立 莫言说,他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李开复说,莫言成功的背后,有一位深明大义的母亲。 莫言在瑞典学院演讲厅发表文学演讲时,讲述了儿时和母亲之间发生的种种故事,字里行间均表现出了对母亲深深的缅怀和思念,透露着对母亲崇高的敬意和无限的感激。由此可见,李开复的说法,可谓是一语中的,恰如其分。 事实也确是如此。 莫言是文学上的巨匠,却生来相貌丑陋,他的长相成了村里村外的人茶余饭后的笑柄,学校里的同学为此也经常合伙欺负他,当他感到痛苦时,母亲便安慰他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母亲的一席话使他找回了生活的自信,也使他对自己有了重新的审视。 母亲曾患了严重的肺病,幼时的莫言常常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寻短见。母亲看出他的心思后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从母亲身上,他看到了坚强,看到了像男人一样伟岸挺拔的巨人形象。正是这种坚强促使他常常不分昼夜的工作、创作,四十年如一日,成为了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进而创造了中国文坛上的奇迹。期间的耐心与毅力,岂是常人所能及,但是莫言坚持下来了。 莫言童年时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扇了母亲一个耳光,并且没收了她们娘俩儿拣到的麦穗。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再次相逢时,年轻的莫言产生了报仇的冲动,母亲的一席话使他放下了攥紧的拳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多么伟大的母亲!多么宽广的胸怀!这也正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所应具备的素质——海纳百川,刚柔兼济,而在潜移默化中,莫言已形成。 母亲对莫言的影响,不仅仅是单纯的说教,有时是默默地表现在具体行动中。中秋节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他们家门口,他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母亲却把自己的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时,他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放学回家时,母亲并没有骂他,但他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 这位伟大的母亲是不识字的,但对识字的人却十分敬重;她一生节俭,却从来没有一次拒绝过儿子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儿子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他;母亲希望他成为一位读书识字的文化人,所以她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满足儿子的学习需求。 莫言的成功,离不开他极高的天赋和后天的努力,但母亲对他的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我们可以想象,假若没有这么一位伟大的母亲,莫言是否能如愿以偿地登上文学的巅峰——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 人们往往惊羡红花的艳丽,却忽视绿叶的陪衬。在莫言成功后的一片欢呼声中,会有多少人能想起曾经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像巨人一样地站在莫言的背后。 (作者系中文系2010级学生) 母 亲 ★蔡 青 我不想用悲伤的笔调 描写你沟壑纵横的前额 那泥土上爬满的蚯蚓 像极了你紧凑的眉心 我还记得那一日下午阳光还算温热 你的背影是一座破落的小屋 我的眼泪是一瓶匆匆下肚的可乐 你走在有风的午日阳光里 像一朵摇摇欲坠的荷 唱着劳作的歌 我想用我温柔的眼泪 化作露珠 点亮你身后的白发 和那一地没发的芽 并不想要刻意想念你 我都没吹奏好一支为你的笛 只是我始终知道 会有一支歌穿过云霄 到达你那里 诉说我对你的味道 (作者系中文系2011级学生) 怀念甘新民老师 ★潘靖壬 中午回家吃饭时,父亲向母亲絮念道:“甘新民老师走了!今年才五十八岁,媳妇没工作,女儿没就业。唉!一个好人就这样走了。今后这一大家子该如何生活下去?原本光景就不是很富裕,现在甘老师又突发疾病,这孤儿寡母今后的日子肯定会更加艰辛。”我耳畔嗡鸣一片,不知该如何下咽。虽在饭桌上与父亲常有拌嘴,这一次却不知怎的,心却隐隐作痛。我少小之时便与先生熟识起来,几日前亦曾相见,孰料那竟变成了最后一次谋面。难道生命如此这般脆弱,脆弱得不能用手碰,害怕会变成了碎沫!总以为死亡永远属于别人,离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十分遥远。 先生早年曾在商洛师专(商洛学院的前身)做过历史系主任、政治系主任,升本后任思想政治教学部主任,工作中认真负责、尽心尽力,生活上一丝不苟、严谨不怠。为学院建设辛苦付出大半辈子,还未到退休年龄就撒手人寰,多么善良的老师,就这样离我们而去。在与病魔斗争的过程中,您肯定特别辛苦吧?那种痛我想只有经历过才会体会。您辛苦付出大半辈子,本该安享晚年了,可是命运总是这么的无情、不尽如意。 记忆退回二十年前。那时的商洛学院并不像如今这么阔大、这么美丽。它耸立在一座荒凉的黄土坡上。每逢雨季,四处泥泞,雨鞋踩出的泥浆使那座本来就不大的校园显得格外昏暗、凋敝。当时的商州,交通也没有今天便达。住在高坡上的师生,小小的出门采购都成了生活中的第一难。先生和师母便张罗了一间小商铺,在当时人眼里,它一点都不亚于而今林立街面的超市。就这么一间小铺子不知道方便了多少人家,但先生从不计较得利,众学生偶有难处也笑言用就是了,钱不打紧的,不打紧。我年幼时经常去买小东西,先生总是推让着不收钱,每每窃喜,回想起来不知占了多少小便宜,生活中的小恩小惠足以令人回味感慨。还没来得及报恩,您就如彗星般如此坠落,这份情谊唯有永存于心。 进入大学之后,很有幸的是先生给我们主讲《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这一门公共课有兴趣者无几,但因少小熟识,所以分外认真。甘老师稳中有变、变中有异的教学模式至今令我难忘,每每一个单元讲罢,总是不厌其烦地让我们勾画重点和难点,交上去的作业每一次都有一大段评语,兢兢业业未见丝毫怠慢,然吾辈顽劣竟未体会先生的良苦用心,着实可惜。 课间时分,偶尔会为先生倒水沏茶,仔细端详茶杯,茶锈萦绕,就这样一个布满茶锈的杯子不知道教育出了多少栋梁之才。这茶锈不仅仅是甘老师生活朴素、节俭的写照,更是走出校园莘莘学子的一份怀念与牵挂。更记得,先生为我们放映《唐山大地震》时,电影情节到了最悲处,我不由得瞧了先生一眼,忽暗忽明中,我看见他的眼泪在眼眶里不停打转。忽然明白,先生也和我们一样,一样脆弱,一样多愁善感。教书育人二十几载,他的每一堂课都是在用生命进行最华丽的演绎。 记得去年暑假,小城连续下了好几天霉雨,淤积在街道角落的雨水久久不能退去。我从驾校练车回来,在学校门口碰见了先生,先生依旧骑着一辆略显破旧的单车,身披一件黄中带绿的雨衣,裤脚高高挽起。我上前去与先生招呼,原来先生是来学校查阅期刊的。这样的天气,对知识依旧如此执着,可想先生定是每天与书为伴。 回想起来,学校组织的每一次大型活动都会看到先生的身影,每当节目精彩之处,先生总是起先鼓掌叫好。 最近的一次碰面是大年初三,相同的地点,不变的单车,永恒的身影,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为永别。很后悔当时没有多聊几句。瘦小的身躯下不知容纳了多少知识与能量!而这些显性的素养殊不知您在私底下付出了多少心血与努力?本想着开学后找机会向先生请教一些问题,孰料,这辈子终究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再见了,我可敬的甘老师,您如斯般的为人师表定会引导学生在人生道路中少走弯路,您对知识的渴望与追求小子定将铭记于心,以您为楷模走完大学这最后的时段。愿您在另一个天堂一切圆满、畅怀。谁的人生都会成为历史,您往回看,您一生的劳顿其实只是为了一件事情的到来——教书育人。这件事您做到了! 很多时候,怀念是一种不可触摸的疼痛,然而只有痛定思痛,才能懂得生活的价值,人生的意义。然逝者已逝,哀痛莫过于生者。愿师母和甜姐姐今后的生活能够一切顺利,早日走出悲痛的阴霾,勇敢生活,绽放出美丽的夏花。 (作者系2010级中文系学生) 关于春天的记忆 ★田家声 谚云:“春打六九头”。癸巳年春早,皇历上的立春时辰是壬辰年腊月二十四日零时十三分,说明蛇年春在年里。立春意味着春天即将到来。人说春天是美好的,不说别的,春天来了的时候,穷汉娃子就不害怕冷了。然而我记忆中的春天与美好无缘,始终与饥饿相伴。 那时候,总觉得春天是漫长的。新年里刚吃了几天饱饭,瓦罐里便米光面净,柜子里也扫不出丁点粮食来了。有道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于是母亲便将冬日里辛苦织就的一匹粗布交给父亲,让他拿到集市换回一点粮食背回家度饥寒。春暖了,地里的野菜就萌生了,我和一帮小伙伴常常挎竹篮到野外剜野菜,拿回家糊饭吃。野菜挖完了,就捋树叶。柳叶、槐叶、榆叶、杓儿叶,都是我们填充饥肠的野(叶)食。有一种叫做“老鸹蒜”的野生植物,也被我们挖回来煮了吃。记得上世纪60年代的“三年困难”的春天,人们将树叶、树皮都吃完了,就挖“观音土”当饭充饥,吃得人个个面带土色,不少人浑身浮肿,用手指在小腿上轻轻按压,立即会陷出一个酒窝状的深坑半天起不来。医学上说那是“浮肿病”,是由缺乏营养造成的。还好,多亏政府拨来了黄豆,分给乡村患浮肿病的大人小孩食,阿弥佗佛,总算没饿死人。我那时大约十四五岁,正是吃饭长身体的时候,却由于极度缺食,饿得皮包骨头,个头也矮挫挫,因此村里人给我起了个“秤砣”的绰号。春季里长天大日头,整天饿着肚皮还要在生产队的地里 “磨洋工”,挣工分。那时讲阶级路线,父亲头上戴了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即使上级偶尔分下来一点返销粮,也永远评不到我家。一次,饿得实实没有办法的我,便趁一个风黑月高的夜晚,悄悄溜出家门,偷生产队“红薯母床”里下的红薯秧子吃。不知怎的让母亲知道了,她将我骂了个鬼吹火,还狠狠揍了我一顿,说咱人穷志不穷,就是饿死也不能做贼偷队上的红薯秧子吃。这事让生产队知道了,罚工分事小,我和你大的脸往哪儿搁?打那之后,我便牢牢记住了母亲的教诲,再不做“偷鸡摸狗”的事了,虽然每年荒春上我们还是总饿肚子。 后来,我有幸考上地区一所中专学校。年年春天,家乡的父老依然打着饿肚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只是越斗越穷,越斗越没有饭吃。我却沾了公家的光,在学校大灶上天天有白馍吃。我因怜悯父母亲,以及几个姊妹伙在春天里挨饿受罪,便每每勒紧裤带,将省下的几斤粮票拿到大灶上全买了“杠子馍”,星期天背回家接济全家,使他们度过三载难熬的春荒。屈指算来,这已经是几十年前的陈年旧事了,但每每回忆起来总令我不寒而栗,眼睛发湿。 年年逢春,今又春到。堂前春燕筑新巢,窗外柳绿桃红,草长莺飞。看如今,家家丰衣足食,处处欢歌笑语。昔日里贫穷落后的面貌早已一去不复返,倘若我的那些已经逝去多载、从未享过幸福的父辈们能够活到今天,不知会高兴成啥样? (作者系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