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贾平凹《秦腔》的独特叙事艺术
文章字数:2,2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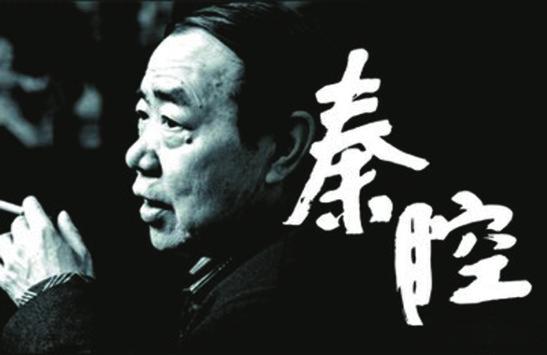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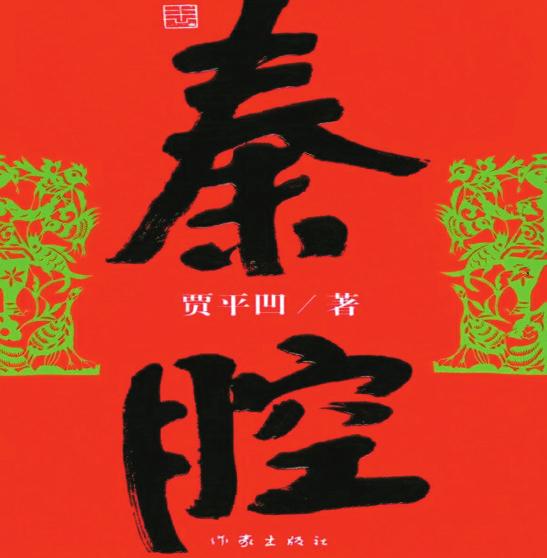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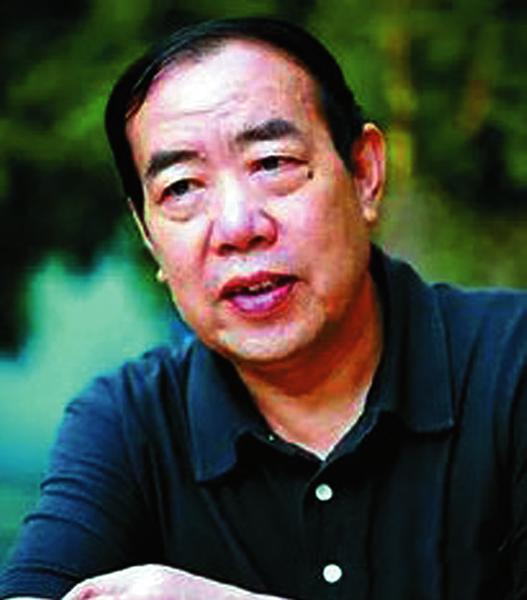

★语言文化传播学院 余琪
像贾平凹的前几部长篇一样,《秦腔》一面世便引起文学界的极大反响。褒扬、赞赏、指责甚至鞭挞,各种看法不一而足,其中争议最大的莫过于该著中作者所采取的与前作不同的叙事手法给阅读者带来的障碍。在《秦腔》研讨会上,多数评论家在发言时,最先表达的是阅读《秦腔》的艰难,认为《秦腔》的最大问题是“叙事琐碎沉重,充满日常化细节,节奏缓慢,内容沉重”。那么造成这种所谓“难度”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如何才能找到这座公园的通幽曲径呢?我们不妨先从它的叙事艺术上来破解。
一、叙事节奏
贾平凹《秦腔》的叙事节奏犹如交谊舞中的慢四步。理解《秦腔》的关键,很大程度上便在理解它的叙事本身。《秦腔》的叙事速度很慢,这样缓慢的叙事速度绝非无因。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样的叙事速度,本身便是对现实变化的感应。《秦腔》所写的是乡村社会的陈年流水账,一年多的时间积累下来,最后的结果却类乎天翻地覆。不知不觉中,乡村生活已然发生了几乎是不可逆转的巨变——让人忧心的巨变:不想让它走的一点点走了,不想让它来的一点一点来了——走了的还不仅仅是朴素的信义、道德、风俗、人情,更是一整套的生活方式和内在的精神;来了的也不仅仅是腐败,来了的更是某种面目不清的未来和对未来把握不住的巨大惶恐。这样的变化,在小说中几乎是不可逆转的情势,并已然形成。
身处在这种变化中的人们,对之并非没有感觉,然而,似乎是现实中的某种因素已经形成了巨大的情势,某些敏感的个人,对这种变化即使有所觉察,却无力阻止情势本身的变化。一切都在变,那种土地上的生活方式和对土地的感情,似乎也面临崩溃,且将永远流失,一去不回。贾平凹就这样沉醉在中场过后的慢四步中,节奏缓慢得似乎感觉不到时间的移动……
二、叙事技巧
《秦腔》用“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握住了《红楼梦》等传统小说日常生活化叙事的根脉,在一定程度上,《秦腔》也借用了《红楼梦》中人物姓名暗指叙事的技巧。《秦腔》中清风街近百号人物组成了一幅长卷浮世图,而其中许多人物姓名符号的指涉意义勾陈出了深层的文本叙事结构。
夏天义老一辈名字按“五常”排行:仁、义、礼、智、信。偏偏老大夏天仁早死,老五夏天信胎死腹中。“掐头去尾”、“无头无尾”的是两个带“人”字旁的字,这寓示着礼崩乐摧之后,人成了空有人形而没人性的两足动物。后来老三夏天礼又中道崩殂,把兄弟的“五常”之序拦腰斩断。
在夏家的下一辈中,人丁较旺的夏天义有五个儿子,夏天义五个儿子道德素质不如狗,而英武一世的夏天义晚年境遇更不如狗。他生养的五个儿子与秦腔名句“窦燕山教五子,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形成强烈的反讽,正可谓:仁义礼智信,金玉满堂瞎。夏天智的儿子夏风对父亲钟爱的秦腔事业表现出不屑一顾的冷漠。夏风是冲出了宗法礼制。
夏家的第三代只有一个女性人物翠翠。翠翠是流行歌手陈星的玩物,而流行歌曲却正与代表传统宗法伦理文化的秦腔相对峙。翠翠的名字饶有寓意:翠翠在《边城》中是淳朴性灵的化身,而在清风街,她却背离了秦腔宣扬的伦理文化,零落成泥碾作尘。翠翠永远地走了。
三、叙事道具
在叙事中,贾平凹善用秦腔乐谱、对联和绘画,进行隔断转换、时空挪移,构筑多维的艺术符号世界。一是秦腔乐谱的穿插。秦人离不开秦腔,一曲曲唱段、一个个曲牌抒发着秦人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秦腔在这部作品里,与碑牌文字在《高老庄》中有异曲同工之妙,结构上能起到隔断转换、时空挪移的作用,尤其能调动欣赏者在旋律和文字之间的同感,从一个新的渠道激发读者的艺术联想和欣赏再创造。在这部小说中,秦腔音乐和锣鼓节奏来渲染人物的心理活动,用来营造气氛,用来表达线性的文字叙述有时难于表达的团块状或云雾状的情绪、感受和意会。这种描写在当代小说中都很少见到。而小说描写的县剧团的炎凉和演员命运的起伏,也成为时代发展和文化变迁的一种症候。在整部小说中,秦声弥散为一种气场,秦韵流贯为一股魂脉而无处不在。它构成小说、小说中的生活、小说中的人物所共有的一种文化和精神质地。二是对联的运用。对联是汉字独有的文学样式,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在《秦腔》中,十多副对联别开生面地构成一种点缀性叙事。赵宏声是《秦腔》中处处应景凑趣的人,他的每一副对联就是一个穿针引线的叙事道具。赵宏声贴出的最后一副对联“来的必有豹变土,去者岂无鱼化才”,则更与《秦腔》乡土叙事终结的寓意紧密呼应。来者如马大中,他像拿着小圆镜侵入马空多的吉普赛人那样在清风街收割着市场化利益,而清风街上的乡土文明也一天天走向“沙化”;去者如夏风之辈,他剥离了秦腔所代表的农耕文化而跃入了都市文明,实现着他的人生价值。三是绘画的补叙。在《秦腔》中,作者绘制的四幅插图与文本构成了互文衬语叙事。“一条线的故事”和“靠在树干上蹭痒痒”两幅插图生动展现了秦 地的乡土文化风貌。“大风”是夏天义热爱土地的生命图腾。最富力度的插图当属“吼秦腔”是夏天义对秦腔文化“满眼衰草无限情”的惋惜!《秦腔》文本中简而有意的墨写式插图更是承袭了“言——象——意”的中国传统绘画式叙事。
《秦腔》创造了不同于作者以往的叙事方法,取得了特别的艺术效果,正因为对这一叙事方法的陌生,人们在阅读时会有些不适应,难免会产生所谓的“难度”。然而,一个艺术家要超越自我,就必须不断地寻找创新之路。塞米利安曾说“赋予不具有形式的素材以形式,这是小说家的艰巨使命”,《秦腔》便完成了这样一次使命。正如作家所言,“如果慢慢去读,能理解我的迷惘和心酸。”的确,唯其如此,我们才能领略文本无尽的妙处,体会作者的独具匠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