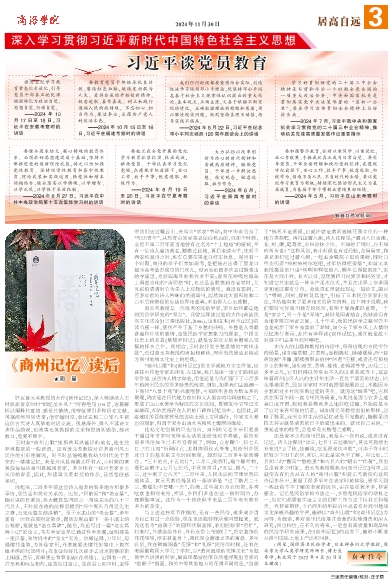《商州记忆》读后
文章字数:3,243

好友黄元英教授的大作《商州记忆》,深入精读清人王时叙旅食京师时“回忆故乡风土”所得绝句104首,逐篇解析以阐释其意境、感受其情绪,他旁征博引多种历史文献,考据商州风俗史事;他穿越时空,尝试去和二百零八年前这位古代诗人真挚地对话交流。 孤悬海外、很久不读诗文类作品的我,也被黄元英教授的文采和思绪所感染,捧读数日,竟爱不释手。
王时叙“商州山歌”里那些耳熟能详的地名,他在注释里提到的一些谚语, 还有黄元英教授对许多商州风土民俗的引申性解说, 时不时总能唤醒我幼少时代关于老家的一缕缕记忆。我是丹凤县商镇北坪村人,小时候的寒暑假每每从商州县城回老家, 多少怀有一些对老家乡土风俗的眷恋,因此,拜读黄元英教授的作品,自然是倍感亲切。
说起来,二百多年前这位诗人提及的很多地方和很多事情,居然是和我有关系的。 比如,“四皓冢”和“尧女墓”,据村里的长辈说,我大概算是四皓之一甪里先生的八十三代后人,王时叙在他的注释里提到“州中周氏乃甪里先生之裔,云先生墓在商洛镇”。 至于东龙山的“尧女墓”,多年前有一次我在那附近散步,偶然发现山脚下一条小溪上的石板桥,竟就是“尧女墓碑”,随后,我还写过一篇“尧女墓碑小记”的论文,考古学家也早已通过科学发掘,证明那是一座汉墓,和传说中的“尧女”无关。 依稀记得,少年时,每遇棣花逢集,为补贴家用,外婆就要去棣花的集市上售卖她手绣的枕顶绣片;我也曾经好几次徒步去过龙驹寨的街上闲逛,然后,再顺便去看看花庙(花戏楼)。 记得有一次,甚至我和玩友相约,还登顶过商山。在商县上初中时,老师带我们去过戴云山、金凤山“学农”劳动;高中毕业后当了“知识青年”,从知青点回家是必经白杨店的,但那个时候,全然不知二百年前当地曾有过名为“十土地庙”的废祠,并有一位诗人遍访耆老,踏勘过此地。再后来读大学,往返于西安和商州之时,班车总要在黑龙口停车休息。 据说有一个时期,商州的学子们参加高考,是把能否出得了黑龙口视为高考是否成功的门坎儿。母亲生前曾多次去过静泉山的寺庙里,为旅居海外的我祈求平安;而我在冲绳的海岛上调查当地的“清明祭”时,也总是会联想到在老家时,父兄叔伯清明时节为先人上坟烧纸的情形。 真没有想到,二百多年前的诗人吟咏的美丽商州,居然如此大面积地和二百年后我曾经的生活世界相重叠,不由得人心生感慨。
黄元英教授是一位优秀的民俗学家,家乡始终都是他的民俗学研究的“原点”。 我曾经拜读过他的大作《商洛民俗文化述论》(三秦出版社,2006),也和这本《商州记忆》的读后感一样,使我产生了基于乡愁的共鸣。 乡愁是人类最普遍和朴实的感情,也是民俗学家想象力的源泉。 中国文化史上的名著《荆楚岁时记》,就是客居北方的南朝梁人宗懔的怀乡之作。 我相信,王时叙抒发乡愁思绪的“商州山歌”,经过黄元英教授的发掘和解读,理所当然地也必将成为商州地域文化史上的经典。
“商州山歌”和《商州记忆》的文学或地方文史价值,应该任由其他专家去评说。在这里,我只是谈一谈它们的民俗学价值。虽然诗人惜字如金,但他还是为我们留下了二百多年前商州民俗的很多珍贵的线索。例如,如果我们去追溯一下商州“八景十观”的兴废继替,可知商州各地为数众多的景观,确实是在历代地方官员和文人墨客的共同建构之下,形成了以山水美学为特征的文化空间, 即便如今它早已支离破碎,却依然残存在人民的口碑和记忆当中。 也因此,商洛地区的百姓常常是把这块土地上文风盛行、 作家文人辈出的现象,归因于家乡山清水秀和风土醇厚的缘故。
比起文化空间的巨变而言, 商州的父老乡亲们更善于通过年节岁时来维系生活的连续性和节奏感, 虽然有很多风俗如今已不再看得到了,例如,立春鞭牛、初七人日、“打儿窝”祈嗣仪式、龙洞祷雨仪式等等,但商州乡民过日子的基本的文化时间框架, 却历经二百多年依然健在。 “三十的火,十五的灯”,二月二,做清明;端午槲叶粽,看忙曲联子;七月七乞巧,中秋夜赏月;“五豆、腊八、二十三,过年剩了七八天”。二百年来,人民生活的节律依然自成体系。 黄元英教授提及的一条谚语是 “过了腊月二十三,娶媳妇不管哪一天”,的确,过年前后为农闲期,各类吃食也相对充裕,所以,乡民们多选在这一段时间内,办理婚娶事宜, 这作为一个传统似乎也是二百年来未曾有多大的改变。
与上述这些年节伴随的,还有一些民俗,或多或少因为自己有过一点体验,现在也还能够鲜活地回想起来。 就说这名为“曲联子”的圆环状锅盔馍,农妇回娘家“看忙”,归来时,外婆会给外孙、外孙女带上“曲联子”,把它装饰的花花绿绿,挂在孩童身上,寄托保全健康之类的寓意。多年以后,我在韩城调查“花馍”和“礼馍”民俗的时候,还有在美国俄勒冈大学孔子学院,以“黄河流域的花馍文化”为题做学术讲演的时候,脑海里都曾经很自然地浮现出老家的“曲联子”锅盔。和关中等其他地方的花馍不同的是,“曲联子”锅盔不是蒸馍,它或许就是黄河流域花馍文化的一种地方类型吧。再说这腊八粥,诗人注释说:“腊月八日食粥,花、树、碾、硙等类,亦皆涂抹少许。 不知始于何时,亦不知何所为也?”这种风俗,我小时候也有过经验,在舅舅家,和表兄弟们吃过腊八粥,一起去涂喂院子里的果树,同时口里念叨着“柿树柿树你吃吧,过年结得疙瘩瘩”,和黄元英教授提及的口诀“树啊树啊吃腊八,明年长得鼓抓抓”,实在是大同小异。长大以后,没想到研习民族学和民俗学,才知道它其实就是一种丰产巫术仪式,并且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分布。 舍妹周虹曾就此写过一篇论文,题目为“喂树、问树、嫁树及其他”,引起了日本民俗学家的关注,并给她寄来了更多相关的研究资料。这个例子说明,我们要研究好商州地方的民俗,有两个视角都很重要,一个是“家乡”,另一个是“异域”,最好是两者结合,能够游刃有余地穿梭在两者之间。 几十年来,我的民俗学之路何尝不也是起步于家乡而漂泊于异域,如今关于家乡风土人情的记忆渐行渐远,此次有幸拜读《商州记忆》,或许就是故土对游子归去来兮的呼唤吧。
在诗人的山歌和教授的诗话中,每每出现的乡民劳作的场景,诸如编草帽、打草鞋;连枷脱粒、碌碡碾场;听“旋黄旋割”开镰,驱犊携犁去抢种“回茬”庄稼,或者还有那些乡土的野味,诸如商芝、香椿、榆钱、老鸦蒜等等,历经二百多年之久,它们仍得以传承至不久的以前甚或当下,这意味着商州山区人民的生计和生活一直处于清苦的状态。民生艰难困苦,民俗学家时不时就需要提醒自己,不能因为乡愁而对乡村民俗做过度的美化。 就说这“酸菜”吧,它居然在两百年间一直为州民所倚重,与其说是因为它多么地爽口或开胃,配起苞谷糊汤多么地好吃过瘾,不如说是为了应对来春可能的饥荒。 诚如黄元英教授指出的那样,忽略了酸菜,商州乡村生活的记忆就是不完整的,腌酸菜的技艺其实就是清苦的日子给逼出来的。 就我自己来说,一想起老家的酸菜,总是难免有酸楚之感啊。
还是有不少的商州民俗,我是头一次听说,或者没有记忆。诗人注释说“谚云,七月十五挂锄钩”,黄元英教授也补充说“立了秋,挂锄钩,吃瓜看戏庆丰收”,可由于我小时候较少下田干农活,所以,对此是完全不了解。 再比如,二月初二的“撒灰”“憋虼蚤”和六月六的“晒衣”“作酱”,我也是没有多少印象。 黄元英教授嘱我为《商州记忆》写序,这就使我有机会从古人的“商州山歌”和黄元英教授的这部诗话作品中,重温了很多早年在老家时的体验,更学习到一些此前并不了解的老家的民俗,实在是收获多多,非常感念。 记忆是民俗学的方法之一,乡愁是民俗学的动机之一,但它们都需要实证主义的田野工作方法予以补正和提升。 我非常期待,今后商州的年轻后生或者有对商州地域文化深感兴趣的学者,能够以“商州山歌”和《商州记忆》为向导、为线索,再对商州民俗展开全面的实地调查和深入研究;我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高质量和高品味的民俗学研究成果,在《商州记忆》的启发下,能够不断地从商州这块土地上产出和问世。
(周星,国际著名民俗学者、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原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本文写于2022年9月20日日本横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