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丘 一 壑 是 怡 颜
文章字数:1,4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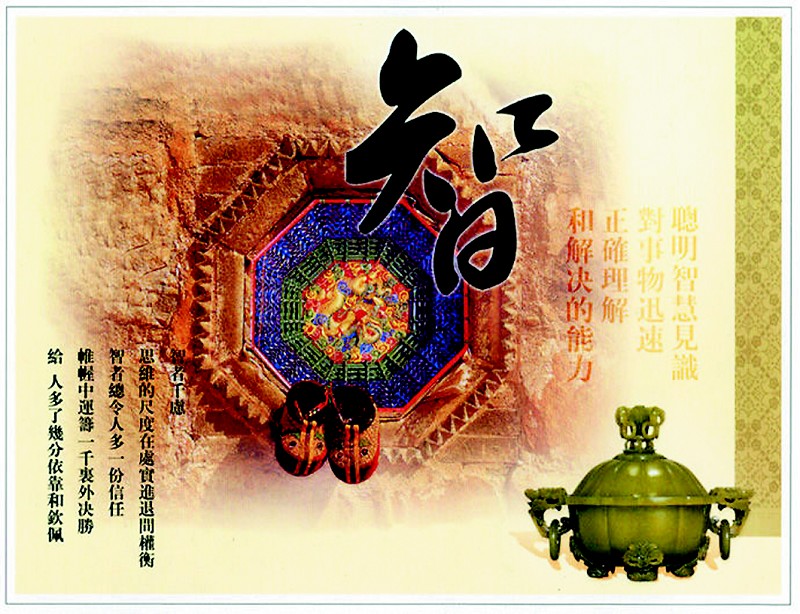
南朝宋初,谢灵运首开山水诗风,为我国诗歌开创了一种新题材。盛唐之际,王维、孟浩然有如双子座辉映诗坛,将山水诗推向极致。有唐以降,山水诗日渐式微。沿至清代,既无大家出现,也少专集问世。然而,嘉庆年间商州诗人王时叙却推出了《商州山歌》104首,以清新古朴的“竹枝词”体和特有的艺术魅力,着力描绘了商州的山水、田园和风俗,给沉寂千年的山水诗坛送来了一曲清歌妙韵。 《商州山歌》“自序”曰:“嘉庆甲戌之冬,旅食京师,言归未能。回忆故乡风土,得绝句一百四首。……以所言皆山中之事,命之曰《商州山歌》。即作竹枝观之,当亦无不可也。”明言其诗主旨在于抒发“旅食京师”的待官游子对“故乡风土”的眷恋赞美之情。此情既不同于谢灵运那种对抗当政、以求在山水中获得慰藉之情,也有别于王维、孟浩然那种隐居山水、体玄悟禅的隐逸之情。因此,王诗有着自己鲜明的风格。 首先,重视把历史事件引入景观。“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历史事件给商州山水增添了历史厚重感和特有的灵性与知名度,能使读者因其历史,产生共鸣。如,《山歌》第87首写“武关胜塞”:“武关岭据四条强,碥路绵延七里长。汉祖由斯先项羽,张仪曾此诈怀王。”一、二句分别暗引战国时,楚国曾在武关附近的四条岭上修有长城;唐贞元7年,上洛刺史李西华新筑蓝田至内乡的商於“碥路”700里,三、四句分别明引刘邦公元前207年由武关入秦,大破秦军于蓝田之南;以及秦襄王公元前299年用张仪计,诱楚怀王武关会盟,后拘之咸阳而死的史实。再如第5首写“丹水环城”:“说是丹朱曾放此,鱼丹几见跃清波。”明引了尧帝子丹朱“顽凶”不肖,而被外放、封于丹水下游的传说。突出商山丹水的历史舞台作用,可以增加读者对其秀美壮丽的认同感。 其次,巧将古人诗句代入写景之中。“商山名利路,夜亦有人行。”战国至清,无数官吏骚人曾经过此,留有不少绝唱。谢灵运写物重视摹写山姿水态,王时叙却善于化名家佳句于诗中,使山水增色,收取名人效应作用。如第6首咏板桥铺:“茅店依然古道旁,板桥今日尚名乡。鸡声人迹温郎路,明月当天满地霜。”巧妙地将温庭筠 《商山早行》“鸡声茅店月,人亦板桥霜。”10字剪裁、融入诗句,显示出板桥独有的文化底蕴。又如第76首吟洛南药子岭:“种药依稀识旧蹊,烧丹约略认幽栖。乱山高下多鸿爪,古路崎岖总雪泥。”最后二句分别剪裁,改易了李涉《再宿武关》“远别秦城万里游,乱山高下入商州”和李商隐《商於新开路》“六百商於路,崎岖古共闻”中的字句化入诗中,不仅起到了典雅之效,而且增强了商州山水的文化感染力。 最后,善以炽热乡情融入字里行间,也是《山歌》的鲜明特色。谢、王、孟诸家多写外地景物,或体道释禅,或彰隐明逸;而王时叙专写故乡山水,抒发爱乡之情。这种炽热情感有时隐约诗中,表现为儿时难以割舍的回忆。如第2首写戴云山:“记得儿时登绝顶,连山浩荡似波流。”第66首写静泉山:“记得前人读书处,七星楼是最高层。”有时则明显袒露笔端,或表现为对他人误解的愤怒,或表现为对自身无奈的遗憾。如第101首:“洪惟元鸟降生商,历有传人土亦香。瘿俗夷音何处是,坡公语病太荒唐。”苏轼仅仅因为给其弟苏辙讲过商州“夷音仅可通名姓,瘿俗无由辨颈腮”,就招来了作者“太荒唐”的指斥。第103首:“一丘一壑是怡颜,况是千山与万山。怅我家斯今老大,空多名胜未跻攀。”此时作者不过三十,竟慨叹年已“老大”,恐无时日尽游故乡山水名胜。一怒、一憾,诗人将其思乡、爱乡情结推向极致,《山歌》主题也由此愈加完美、深化。 原载于 《商洛学院》2006年12月1日第60期第3版《商洛文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