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州初录》里的文学地理
文章字数:2,1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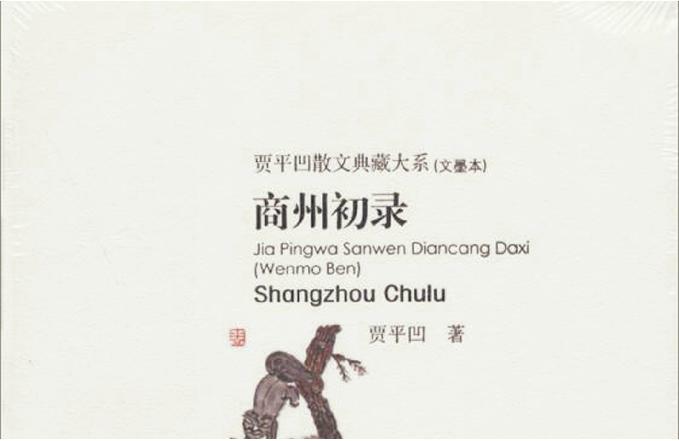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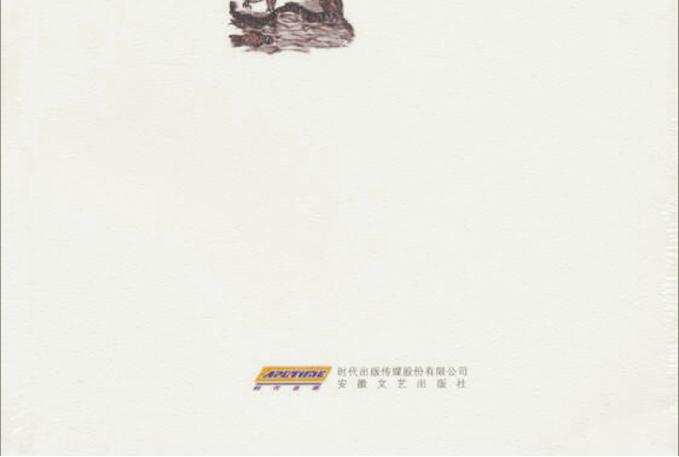
★语言文化传播学院教授程华
《商州初录》写于1984年,距今已30多年,穿过30多年的创作道路,如今回头重新看这部作品,仍能看出很多新意。
一句成语叫纲举目张,贾平凹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他整部文学创作的纲,如同《狂人日记》之于鲁迅,《透明的红萝卜》之于莫言,在这部作品中,有诸多文学的因素被贾平凹在其后的创作过程中不断放大和完善。
首先是创作的视角。在这部作品中,贾平凹具有鲜明的文化意识,在此之前的小说,可以说都是作者的试笔:学习如何寻找素材,有城市题材,更多山村故事,但仅止于呈现美丽的山村背景;如何在素材中表达想法,而这想法也不过是寻找美好的人情人性,试笔阶段的作者大多会把社会和人性想得比较美好;如何安排结构,结构的起承转合,有故事、有情景、有心理,这些都是塑造人物的依据等等。也就是说,作者还在模仿或是学习别人是如何写小说的,他自己并没有关于好小说的观念。在《商州初录》中,我们看到,贾氏有了自己的视角,这个视角很明显,就是要给读者呈现专属于自我独有的故乡的山川地理、民俗风情,这是地域文化的独特表现。贾平凹认为,地域文化可以彰显作品的独特性。在全国主流文学热衷于“伤痕”“反思”潮流的背景下,贾先生通过文学呈现家乡独特的地域文化,就是非常宝贵的文化视角。《商州初录》只是很单纯的呈现具有原始、隐秘风情的地域文化。从关注地域文化到在地域文化的演变发展中,表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对立与冲突,文化视角是贾平凹小说最可宝贵的写作视角。
其次,从写作的情感而言,饱含着从农村走出的知识分子对自己故乡的眷恋和赞美。《初录》是知识分子游历故乡的游踪日记,14篇短文,多数篇幅记写故乡的山川地理和风情,其中融入了家乡的民俗风情。故乡虽贫瘠、落后,但作者对此充满热爱。对于一个从未到过商州的人,读者感受到的是一个未经开发的充满原始浪漫气息的地方;对于一个长久生活在此地的读者,能感受到作者字里行间满溢着真情,也只有这样的真情,你才会觉得,作者笔下的自然山水、人情物理、民俗掌故,甚至方言土语是如此的熟悉和亲切,换一种词,换一种说法,都不足以表现故乡的美,这样的真实,没有真情是无法传达的。在这部作品里,贾平凹对故乡的钟爱,恰似一个青春幻梦般的少年对恋人的爱般执着。作者笔下的故乡景象神秘悠远、浪漫放达,作者笔下的山地人物淳朴善良。自此文之后,30多年来,贾平凹始终未曾离开以故乡为基础的创作,从写故乡的山川地理、民俗风情开始,贾氏写故乡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写故乡的现代变迁、写故乡农民工的命运,写故乡基层政府和老百姓的冲突,写故乡百年的历史变迁。贾先生本是农民,但从农村出走,40年的城市生活,使贾平凹成长为理性成熟的知识分子,用知识分子的立场为所钟情的故乡写作,是贾平凹文学创作的自觉阶段。
从行文结构来看,《商州初录》散文化的叙事结构,是贾平凹突破戏剧化传统小说结构模式的一次尝试。虽是尝试,但作者行文利落、整体结构混沌洒脱。贾平凹重视感觉,强调立意,善白描化的语言,字里行间传情,是诗化的小说作者。《商州初录》介于散文和小说之间,少数篇幅是有故事的散文,多数是在游踪式的山川和民俗的介绍中插入传奇和闲笔。这一写作方式,和贾平凹的文风和性情相谐和。在写完《浮躁》后,贾平凹就放弃了这种倚重故事的情节小说,强调意象在小说中的运用。可以说,在转了一个小圈之后,贾平凹又回到了《商州初录》的这种结构模式中。从《妊娠》《太白山记》以至《废都》《秦腔》《古炉》,贾平凹逐渐形成类似闲话体的小说文体,这是《商州初录》中早已呈现的,是更为自由的叙事文体。这就说明,作者苦苦寻找的艺术结构,往往是冥冥之中的,适合自己情感和性情的艺术结构。
语言与作者个性最契合,语言是一切文学写作的目的。《商州初录》中的语言是抒情的,它是作者诗人化抒情气质的外现,同时,《初录》中的语言多方言的加入,它表明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已经具有初步的语言感悟。此时的贾平凹已经意识到语言和语言所表现对象的一致性。用方言呈现商洛的风俗和文化,民情和民性,应该是从《初录》开始的。但在《初录》中,方言并未形成一种叙事的腔调,方言词汇只是彰显地域文化的一种手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商州系列小说中,贾氏书写商州现实生活的系列作品,方言味浓厚,初显口语腔调;书写商州传奇故事的系列作品,有传统文人笔记腔调。笔记体的叙事从《初录》,到《五魁》《美穴地》直至《废都》,臻于成熟。《废都》中的文人笔记体叙述腔调,与废都城里的知识分子生活相谐和。随着写作题材的变化,贾氏转换语言腔调,在《高老庄》中大量使用方言,甚至罗列方言,凸显方言的粗糙,有评论者认为,从《高老庄》始,贾氏的写作可称为方言腔调,贾平凹自觉脱去了知识分子的外衣,隐去了自己在小说中的身份,取故事中的人物作为小说的叙事者,诸如《秦腔》中的引生,《高兴》中的刘高兴,《古炉》中的狗尿苔,《老生》中的老生,叙事者、叙述的人物、叙述的背景以及叙述的语言,自然融为一体。从在作品中渗透方言到真正用方言思考和叙述,对方言的运用还要追溯到《商州初录》。
莫言认为,一个作者的写作风格主要表现在题材的选择、作者的文学立场、文体结构的趋向和语言特点等几方面,贾平凹文学风格的初步显现正是由《商州初录》始,由此出发,贾氏建造了丰富厚重的商州世界文学大厦,这个大厦的底座就是《商州初录》,它结实而美丽,有无限生长和生发的可能。



